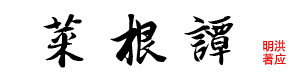1 莫罗兹卡
莱奋生走下台阶,到了院子里,他那把刀鞘撞瘪了的日本军刀在阶磴上碰得锵锵作响。田野里飘来一阵阵荞麦蜜的气息。头顶上,七月的太阳在炎热的、浅粉红色泡沫似的云朵里缓缓浮动。
传令兵莫罗兹卡在摊开的苫布上晒燕麦,一面用鞭子轰赶一群可恶的珠鸡。
“把这个送到沙尔狄巴的部队里去,”莱奋生把一件公文交给他,说。“告诉他……不,不用了,里面都写了。”
莫罗兹卡不大高兴,他把头一扭,轻轻地抽着鞭子。他不愿意去。他讨厌这些枯燥乏味的出差和没有人需要的公文,他最讨厌的是莱奋生的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。这双又大又深的眼睛象湖水,把莫罗兹卡连人带靴子统统吸了进去性”。,并且在他身上看到许多连莫罗兹卡自己恐怕也未必意识到的东西。
“坏蛋,”传令兵心里想,一面眨巴着眼睛,好象受了委屈似的。
“你干吗站着不动?”莱奋生发火了。
“你这是怎么回事,队长同志,不论到哪儿去,一开口就是莫罗兹卡。好象除了我队里就没有别人了……”
莫罗兹卡故意称他“队长同志”,好显得正式些,平时他只叫他的姓。
“那末是要我自己去吗,啊?”莱奋生挖苦地问。
“干吗要你自己去?有的是人……”
莱奋生觉得这种人实在不可理喻,只好态度坚决地把公文往衣袋里一塞。
“去把枪交还给军需主任,”他口气极其平静他说,“交了枪,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。我这儿不需要捣蛋鬼……”
河上吹来的和风拂乱了莫罗兹卡的不听活的头发。在仓库旁边焦干的苦艾丛里,不知疲倦的纺织娘好象在锤打着赤热的空气。
“别急嘛,”莫罗兹卡绷着脸说。“把信给我。”
他把情往怀里揣的时候,与其说是对莱奋生,还不如说是自言自语地解释说:
“叫我离队,绝对办不到,把枪交出去那更不行。”他把满是尘土的军帽推到后脑上,说到未了,声音忽然变得高兴和响亮起来:“我们来干这个,可不是为了你那双漂亮眼睛,我的朋友莱奋生!……我照矿工说话那样干脆地对你说吧!……”
“这才象话呀,”队长笑了起来。“可是起初你硬是不肯去……笨蛋!”
莫罗兹卡掀着莱奋生的一个钮扣把他拉过来,压低嗓门,好象谈什么秘密似他说:
“我啊,刚要到医院去找瓦留哈①,什么都准备好了,可你偏偏要送公文。所以,你自己才是笨蛋呢……”
【①莫罗兹卡的妻子瓦丽亚的小名。——译者注。】
他调皮地夹了平一只绿褐色的眼睛,噗哧一笑,直到现在,只要一提到妻子,他的笑声里就会流露出猥亵的音调,象是年深日久的霉斑又显现出来一样。
“季莫沙!”莱奋生朝着台阶上一个没精打采的小伙子叫了一声。“你去看着燕麦;莫罗兹卡要出去。”
在马厩旁边,爆破手冈恰连柯骑在一只倒扣着的马槽上,修补皮驮袋。他的光脑袋晒得黑红,脸色好象打火石,深色的胡子象毛毡似的紧粘在一块。他低着头在缝驮袋,他用起针来好象在挥动草耙,有力的肩胛骨在粗麻布衣服下面磨盘似的转动着。
“你怎么,又要出去啦?”爆破手问道。
“正是,爆破手老人家!……”
莫罗兹卡挺身立正,举起手来随便贴近什么地方一放,敬了个礼。
“稍息,”冈恰连柯宽容他说。“从前我也是象你这么愣。派你出去于什么?”
“屁事;队长叫我去活动活动。他说,不然你会在这儿生出一群娃娃啦。”
“傻瓜……”爆破手正用牙齿咬断麻线,说话发音不清,“苏昌的贫嘴。”
莫罗兹卡从棚子里牵出马来。那匹鬃毛很长的小公马,警觉地两耳直竖。它长得结实,毛很长,跑得快,样子象主人:也有那么一对绿褐色的发亮的眼睛,也那么矮小敦实,罗圈脚,也有些愣,但又调皮,爱捣乱。
“米什卡……唔,唔……你这个魔鬼啊……”莫罗兹卡边拉紧马肚带,一边爱怜地唠叨着。“米什卡……唔一嗝……上帝的小畜生……”
“要论你们俩的脑袋谁的管用的话,”爆破手一本本经地说。“你就不该骑米什卡,倒是应该让米什卡骑你,那才是正理。”
莫罗兹卡上了马,快步跑出牧场。
紧挨着河边有一条野草丛生的村路。对岸伸展着一片浴着阳光的荞麦田和小麦田。锡霍特一阿林山脉的蔚蓝色寒仿佛在温暖的水气中颤动。
莫罗兹卡是第二代的矿工。他爷爷--一个受他自己的上帝和众人欺侮的苏昌老大爷--还是种地的;到他爹手里就用煤代替了黑土。
莫罗兹卡出生在二号矿井附近一座昏暗的木头房子:那时嘶哑的早班汽笛正在呜呜地响着。
“男孩?……”矿上的医生从小屋里走出来,告诉做父亲的,生下来的不是别的,是个儿子,做父亲的重又问了遍。
“那就是第四个啦……”父亲用无可奈何的口吻计算,“这个日子可快活啦……”
说完之后,他就套上满是煤灰的防雨布上装,上工了。
到了十二岁,莫罗兹卡已经习惯了听到汽笛就起床,学了推土斗车,说些无聊的;多半是骂人的租活,喝烧洒。苏昌矿场的小酒店并不比井架少。
离矿井大约一百来俄丈的地方,是山沟的尽头,丘陵地带的起点。长着一层苔藓,木质坚实的云杉,从这里森严地俯视这个村镇。每逢灰豪蒙的有雾的早晨,原始森林里的马鹿便拼命叫唤,想盖过汽笛的声音。装煤的平车,顺着绵延不断的轨道日复一日地穿过山岭之间苍绿的鲫隙,越过陡削的山隘,向康沟子车站爬去。山脊上涂着黑油的绞盘卷着溜滑的缆索,由于经常的紧张而抖动。在山隘脚下芬芳的针叶林里,随随便便造了儿所砖屋,有人在那里不知为谁干活,有几个“杜鹃”①鸣着音调不同的汽笛,还有电力起重机在嗡嗡地响着。
【①一种小型机车,因为汽笛声象杜鹃啼声而得名。——译者注。】
生活的确是很快活。
在这种生活里,莫罗兹卡没有去寻找新的大道,而是走着前人走过的稳妥的小路。后来,他买了一件充缎子的衬衫和一双喇叭口的小牛皮皮靴,逢年过节就去山村里游逛。跟那里的年轻人一块拉手风琴,跟小伙子们打架,唱黄色小调,“带坏”乡下的姑娘。
在归途中,“矿上的人”常到瓜田里去偷西瓜和圆滚滚的牟罗玛黄爪,跳到水流湍急的溪涧里洗澡。他们的快活而响亮的声音惊动了原始森林,惹得一弯残月从山岩后面艳羡地窥望。河上飘动着温暖的夜的湿气。后来,莫罗兹卡被关进散发出霉味、包脚布臭味和臭虫气味的警察署。这事发生在四月罢工的高潮期间,那时候,浑浊得象矿下瞎马的眼泪似的地下水,日以继夜地顺着井简滴出来,谁也不去抽它。
他坐牢倒不是因为他干了什么了不起的英雄事迹,而只是因为他喜欢信口开河。他们想吓唬吓唬他,希望能从他嘴里探听出带头罢工的人。莫罗兹卡跟蚂蚁河上一批私酒贩子一同关在一个臭气熏人的牢房里,对他们讲了无数淫猥的故事,却没有泄露罢工领袖们的名字。
后来,他上了前线--被编进骑兵队。他在那里,象所有的骑兵一样,学会了瞧不起“步行的马”①,他六次挂彩,两次被震伤,在革命前就完全被免了兵役。
回家之后,他连续狂饮了大约两个星期,后来跟矿上一号井的一个善良而放荡的、不会生育的推车女工结了婚。他做事向来不加考虑,在他看起来,生活是简单的,毫无奥妙,就象苏昌瓜田里滚圆的牟罗玛黄瓜一样。
也许是因为这样,一九一一八年他带着老婆一起保卫苏维埃去了。
不管是为了什么,反正从此就不准他回到矿上去了,因为苏维埃没有能支持住,而新政权②是不太瞧得起这类人的。
【①指步兵。——译者注。】
【②指当时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政权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,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,以高尔察克为首,在乌拉尔、西伯利亚及远东建立反革命军事独裁政权,一九二○年初被红军消灭,译者注。】
米什卡生气地跺着钉了掌的蹄子;橙色的马蝇一个劲儿在它耳旁赡赌地叫,钻进它的毛茸茸的毛里,一直把它叮得出血。
莫罗兹卡骑马来到斯维雅基诺故斗区。克雷洛夫卡村被茂生着翠绿的榛树的丘陵所掩蔽,不见影踪;沙尔狄巴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。
“兹-兹-兹……兹-兹-兹……”马蝇烦人地尖声叫着。
忽然,一个奇怪的炸裂声震动着空气,在丘陵后面滚过去。接着,又是第二声,第三声。……好象有一头挣脱了索链的野兽,在多刺的灌木丛中乱跑乱窜。
“别慌,”莫罗兹卡勒住缰绳,几乎听不出地说。
米什卡把茁壮的身子朝前一冲,乖乖地不动了。
“听见没有?……在打枪!……”传令兵挺直身子,激动地嘟哝说。“在打枪!……是吧?”
“嗒-嗒-嗒……”机枪在丘陵后面响起来。炮火好象是一根线,把别旦枪震耳的轰隆声和日本卡宾枪刺耳的哭泣声串连起来。
“快跑!……”莫罗兹卡用紧张激动的声音喊着。
他的脚尖习惯地深深伸进脚蹬,哆嗦的手指打开了手枪套,这时米什卡已经越过发出炸裂声的灌木丛,向山顶冲去。
还没有登上山脊,莫罗兹卡就把马勒住。
“你在这儿等着,”他跳到地上,把缰绳扔在鞍桥上,说。米什卡是忠实的奴隶,不用拴。
莫罗兹卡匍匐爬上山顶。右边,有一队军帽上带黄绿色帽箍、样子相同的小矮人,排成整齐的散兵线,象检阅时那样熟练地绕过克雷洛夫卡跑着。左边的人们仓皇失措,三三两两地在麦棚金黄的大麦丛中乱跑,边跑边用别旦枪还击。(沙尔狄巴、莫罗兹卡根据黑马和尖顶獾皮帽认出是他)暴跳如雷,进四面挥舞着鞭子,但不能把人们拦住。可以看到,有些人在偷偷地把红带子撕掉。
“这些败类,是在干什么,这是在干什么。……”莫罗兹卡喃喃他说,双方的射击使他愈来愈兴奋。
在后面仓皇逃跑的那一小堆人里面,有一个瘦弱的小伙子,用手帕包扎着伤口,身穿城里式样的瘦小的上衣,笨拙地拖着步枪,微肢地奔跑着。别人不愿意把他一个人甩下,显然是有意迁就他的速度。这一堆人很快地稀少下去,那个包扎着白布的小伙子也倒下了。但是他没有被打死他几次挣扎着要起来,要爬、他伸出双手,嘴里不知在喊着什么。
人们撇下了他,头也不回地加快步伐跑了。
“这些败类,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呀!”莫罗兹卡紧张地用手指紧攥着满是汗水的卡宾枪,又说了一遍。
“米什卡,这儿来!……”他喊的时候嗓音突然变了。
身上被磨出了血的小公马,呼味呼陆地扇动着鼻孔,轻轻嘶叫了一声,跳上山顶。
几秒钟后,莫罗兹卡就象展开翅膀的鸟儿那样在大麦日里飞驰。枪弹象马蝇似的,凶狠地在头顶上嘘嘘掠过,马背常常象是落进深渊,脚底下的大麦拼命地唿哨着。
“卧倒!……”莫罗兹卡喊了一声,把绍绳甩到一边,一只脚拼命用马刺刺马。
米什卡不愿意在弹雨下卧倒,它四蹄腾空,围着那个头上.白绷带染着血、仰卧着呻吟的人乱跳。
“卧倒……”莫罗兹卡嘎声喊着,几乎要用嚼子勒磁马嘴。米什卡把紧张得发抖的双膝一屈,伏在地上。
“痛啊,啊呀……好一痛啊!”传令兵把受伤的人横放在马勒上的时候,那人呻吟着说。这小伙于面色苍白,没有胡须,脸上虽然有血污,却显得干干净净。
“别嚷,讨厌的东西……”莫罗兹卡低语说。
几分钟后,他放开缰绳,双手托着马背上的人,绕过丘陵,
- 360安全浏览器
- QQ浏览器下载
-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
- 七剑十三侠
- 三剑客
- 三国演义
- 三遂平妖传
- 上海鲜花店
- 东周列国志
- 东游记
- 九命奇冤
- 乾隆下江南
- 争春园
- 二刻拍案惊奇
-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- 五美缘全传
- 交际花盛衰记
- 倩女离魂
- 傲慢与偏见
- 儒林外史
- 儿女英雄传
- 元代野史
- 八段锦
- 初刻拍案惊奇
- 包法利夫人
- 北回归线
- 北游记
- 十日谈
- 千年修仙记
- 南回归线
- 双城记
- 变形记
- 合浦珠
- 名利场
- 后宋慈云走国全传
- 听月楼
- 吴江雪
- 周朝秘史
- 呼啸山庄
- 咒枣记
- 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
- 唐诗三百首
- 喧哗与骚动
- 喻世明言
- 围炉夜话
- 在人间
- 型世言
- 基督山伯爵
- 堂吉诃德
- 增广贤文
- 声律启蒙
- 大卫·科波菲尔
- 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
- 大清三杰
- 天工开物
- 失乐园
- 女娲石
- 好逑传
- 孽海花
- 守弱学
- 安娜·卡列尼娜
- 官场现形记
- 定鼎奇闻
- 宫女卷
- 封神演义
- 小窗幽记
- 局外人
- 山海经
- 巧联珠
- 巴黎圣母院
- 平山冷燕
- 幻中游
- 幻灭
- 幼学琼林
- 幽谷百合
- 度心术
- 引凤萧
- 归莲梦
- 德伯家的苔丝
- 快士传
- 快眼看书首页
- 恨海
- 悲惨世界
- 情梦柝
- 我是猫
- 我的大学
- 战争与和平
- 断鸿零雁记
- 新编绘图今古奇观
- 日瓦戈医生
- 明心宝鉴
- 明月台
- 春阿氏谋夫案
- 智囊全集
- 智除巨阉
- 曾国藩家书
- 最后的莫希干人
- 木兰奇女传
- 李鸿章与慈禧
- 杨乃武与小白菜
- 杨家将
- 格列佛游记
- 格言联璧
- 桃花扇
- 梅兰佳话
- 梦中缘
- 欧也妮·葛朗台
- 毁灭
- 母亲
- 水浒传
- 水浒后传
- 洗冤集录
- 洛丽塔
- 济公全传
- 浮生六记
- 海上花列传
- 海游记
- 清平山堂话本
- 源氏物语
- 漂亮朋友
- 牛虻
- 物种起源
- 狐狸缘全传
- 玉娇梨
- 玉梨魂
- 理智与情感
-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
- 生花梦
- 白痴
- 百年孤独
- 百度
- 百战奇略
- 百花野史
- 石家庄网站建设
- 禅真逸史
- 窦娥冤
- 童年
- 第一美女传
- 第二十二条军规
- 简·爱
- 素书
- 红与黑
- 红楼梦
- 约翰·克里斯朵夫
- 终须梦
- 续金瓶梅
- 绿野仙踪
- 罗织经
- 罪与罚
- 老人与海
- 老残游记
- 老残游记续集
- 花月痕
- 英云梦传
- 茶花女
- 草木春秋演义
- 荡寇志
- 荣枯鉴
- 荷马史诗
- 蕉叶帕
- 薛刚反唐
- 蝴蝶媒
- 西游记
- 西游记补
- 警世通言
- 论衡
- 说岳全传
- 贝姨
- 辛弃疾
- 这书能让你戒烟
-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
- 追忆似水年华
- 道德经
- 邦斯舅舅
- 醒世姻缘传
- 醒世恒言
- 醒名花
- 醒梦骈言
- 金云翘传
- 金瓶梅传奇
-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- 镜花缘
- 长春真人西游记
- 隋唐演义
- 雪月梅
- 雾都孤儿
- 青年近卫军
- 静静的顿河
- 韬晦术
- 风月梦
- 风月鉴
- 风流悟
- 飘
- 飞花艳想
- 飞龙全传
- 马丁·伊登
- 驻春园小史
- 高老头
- 鬼谷子
- 鲁滨逊漂流记
- 鸳鸯针
- 麦克白
- 麦田里的守望者
- 龙文鞭影
- >>更多作品